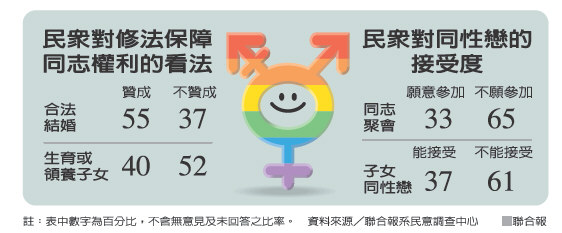每個人小時候都有過自己的秘密基地吧。
我讀小學的時候,剛好遇到學校新舊校舍交替期,舊大樓只剩一些辦公室還在使用,學校禁止學生進入,反而讓更多學生想進去「探險」。我至今仍記得,那天午休,我走進舊大樓天井時,一位八歲的男孩感受到人生中第一次「平靜」,那不只是一種聽覺上的安靜,而是可以脫離老師、父母、同學,完全與外界隔絕、被世界遺忘的那種寧靜。那是我的第一個秘密基地,直到我畢業前一年的暑假,舊大樓才帶著男孩的秘密一同被拆除,成為廢墟、夷為平地。
所謂「秘密基地」不一定要位置很隱密,而是可以藏著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的自己,是可以放鬆內心的警戒與偽裝、不須遮掩自己的脆弱與傷口的地方。在秘密基地裡的我們,得以擺脫外界各式各樣銳利的眼光,可以毫無保留的把自己給攤平,就算心裡住著一隻的怪物也沒關係。
是枝裕和新作《怪物》正是講一個關於兩個孩子共享一個秘密基地的故事。
是枝裕和回歸日本之作,攜手坂本龍一共譜溫柔的成長之詩
是枝裕和的作品始終圍繞著「家庭」命題,《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》是一群被拋棄的孩子相依為命的家;《海街日記》是四位同父異母的姊妹組成的家;《小偷家族》則是一個沒有血緣關係、為了生存湊合而成的家。是枝裕和擅長描繪家庭的多元面貌,挑戰所謂親情與血緣的傳統,並從中找出人與人的羈絆與情感。
拍了這麼多年的日本家庭,是枝裕和或許也有些膩了,於是他在2018年以《小偷家族》獲得坎城金棕櫚獎後,決定跨出日本,到法國拍攝他的第一部外語片《真實》,講一對法國母女的矛盾;又到韓國拍攝《嬰兒轉運站》講兒童棄養與販賣的議題。
走出國際,似乎是許多導演走到一個階段後自我突破的嘗試,香港導演王家衛年近半百時,到法國拍攝《我的藍莓夜》;台灣導演侯孝賢也在花甲之年去法國拍了《紅氣球》。有趣的是,跨國合拍電影的評價,都不比他們在母國的作品來得出色,因此這幾位名導會再「回歸」母國。王家衛回歸香港後交出《一代宗師》;侯孝賢回歸台灣拍了《刺客聶隱娘》;是枝裕和則在回歸日本後,完成了《怪物》。
《怪物》由是枝裕和執導、坂元裕二編劇、坂本龍一配樂,這次電影的節奏比是枝裕和過往的作品變得更為明快緊湊。除了關注家庭內部的矛盾,更進一步討論了外部的校園教育體制的僵化,以及個體面對同儕壓力下,特別是在日本這樣重視團隊精神的國家,個人如何在「合群」與「獨特」間做出抉擇。
為了「合群」必須偽裝自己內心獨特的怪物
《怪物》的主角麥野湊是一個平凡的十歲男孩,他的父親幾年前剛過世,剛好是在他無法假裝不記得,又還未真正理解死亡的年紀。
父親死後,湊的母親早織更加保護他,時時刻刻都關心著湊的一舉一動,即使在工作和育兒之間忙得心力交瘁,仍全心全意想扮演好母親的角色。早織很擔心兒子,湊常常出現怪異的行為:自己在浴室剪頭髮、水壺裡裝了石頭、鞋子少一隻,還有一次晚上沒有回家,一個人在廢棄的隧道裡玩,喃喃自語地說:「怪物是誰?」
早織一再追問之下,湊才囁嚅地說,學校新來的保利老師會打他、說他腦袋裡裝著「豬腦」。早織隔天就到學校去跟校長興師問罪。保利老師再三道歉,仍被學校強迫解雇,但他始終沒有弄明白,湊為什麼要說謊,因為湊說的那些事,根本不曾發生。
其實「怪物是誰?」只是麥野湊跟好友星川依里兩人在秘密基地玩的一個秘密遊戲。他們會用一組動物卡牌,輪流抽一張貼在頭上,自己不能看,只能透過問對方問題,猜出自己抽到的是什麼動物。
在電影裡,這個遊戲具有隱喻性,只能透過別人的說詞認識自己(怪物)。就像美國社會學家顧里提出的「鏡中自我」理論:人必須透過外在的他人才能認識自己。在一段又一段的人際關係裡,或許我們真正想知道的不是認識「對方是誰?」,而是認識「我是誰?」這是湊一直想不通的問題。
星川依里是麥野湊的同班同學,他沒有媽媽、爸爸工作又很忙,幾乎是自己養育自己長大。他在學校不太「合群」,總是和女孩玩在一起,班上其他的男同學都會欺負他,而依里也不還手、不會跟老師告狀,他也沒有試圖想改變自己奇怪又獨特的一面,只是逆來順受、默默地承受著這世界無所不在的惡意。
湊曾經為了「合群」假裝欺負過依里,其實湊一點也不想欺負他,但也不敢跟依里一起玩,湊害怕如果跟依里要好的話,他也會惹上麻煩、被班上其他男生欺負。他只好表面上欺負依里,然後再私下跟依里道歉,而依里總是會原諒他,因為依里是如此善良無害。
隨著兩人的感情愈來愈緊密,湊也愈來愈難隱藏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,他無法忽視內心對依里的喜愛,他在依里身上看見了真實的自己,他害怕母親期待他「成家立業生小孩」,他擔心如同怪物的自己此生都無法得到幸福。因為恐懼外界異樣的眼光,他說不出這些秘密,只能藏在秘密基地裡。
他們的秘密基地是一輛廢棄電車,他們把純真與快樂全部留在那裡。湊跟依里只會在秘密基地當好朋友,離開了秘密基地,兩人就變回陌生人。這段友情成為他們兩人共同藏在秘密基地裡的秘密,卻是湊最開心的時光,他可以擺脫同儕的壓力、不用在乎母親和老師的關愛,可以毫無保留、成為真正的自己。
搭著那台不會動的破舊電車,他們能一同前往一個遙遠的、無憂無慮的地方。
「怪物是誰?」電影給我們看見,我們看不到的東西
《怪物》一共分成三段,三段故事的開頭都是同一場大火、結尾則都是同一場颱風。時間線相同,但是故事的視角不同,第一段是湊的母親、第二段是湊的老師、第三段是湊自己,三個人物的不同視角,交織出一個立體、複雜,卻又純真的成長故事。
三段敘事特別能展現出每個人視角的侷限性,因為每個人都只能知道一部分的事實,無法看見整個事件真實的全貌。人們總是習慣只用有限的資訊,就去判斷是非對錯,去替自以為是的正義發言,這正是社群網路時代、資訊破碎化下,我們最常犯的錯。
是枝裕和曾說,現代人很難客觀看待世界,大半只從自己的角度思考,社交媒體上常常是見樹而不見林,人們相互攻擊,只接受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。
正因為社交媒體上的意識形態如此壁壘分明,不同的立場的衝突變得極端對立,只要意見與自己不同,就是敵人,失去了中間的模糊地帶,也失去了客觀討論的空間。所有人在網路上都跟湊一樣,會被社群風向給綁架、必須選邊站,只能成為一個僵化死板的「人設」,隱藏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。
當每個人的視野愈來愈狹隘,電影也就變得更加重要。正如同楊德昌導演在《一一》中的經典台詞:「 我要去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,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。」電影讓我們看見故事的全貌,讓我們能夠看清楚自己。
在《怪物》這部電影裡,我看見了幾乎遺忘的小時候的自己,那個躲在秘密基地裡,開心跟怪物共處的自己。長大後我們愈來愈擅長隱藏心底的怪物,削去突出的犄角,學習偽裝與合群、變得跟大家一樣。
隱藏久了,心底的怪物有一天會無聲無息地消失不見,想要找也找不回來了。是枝裕和透過電影溫柔地對孩子說:沒有關係的,就帶著怪物一起放心地往前奔跑吧,一直跑一直跑,總會抵達一個能安放自己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