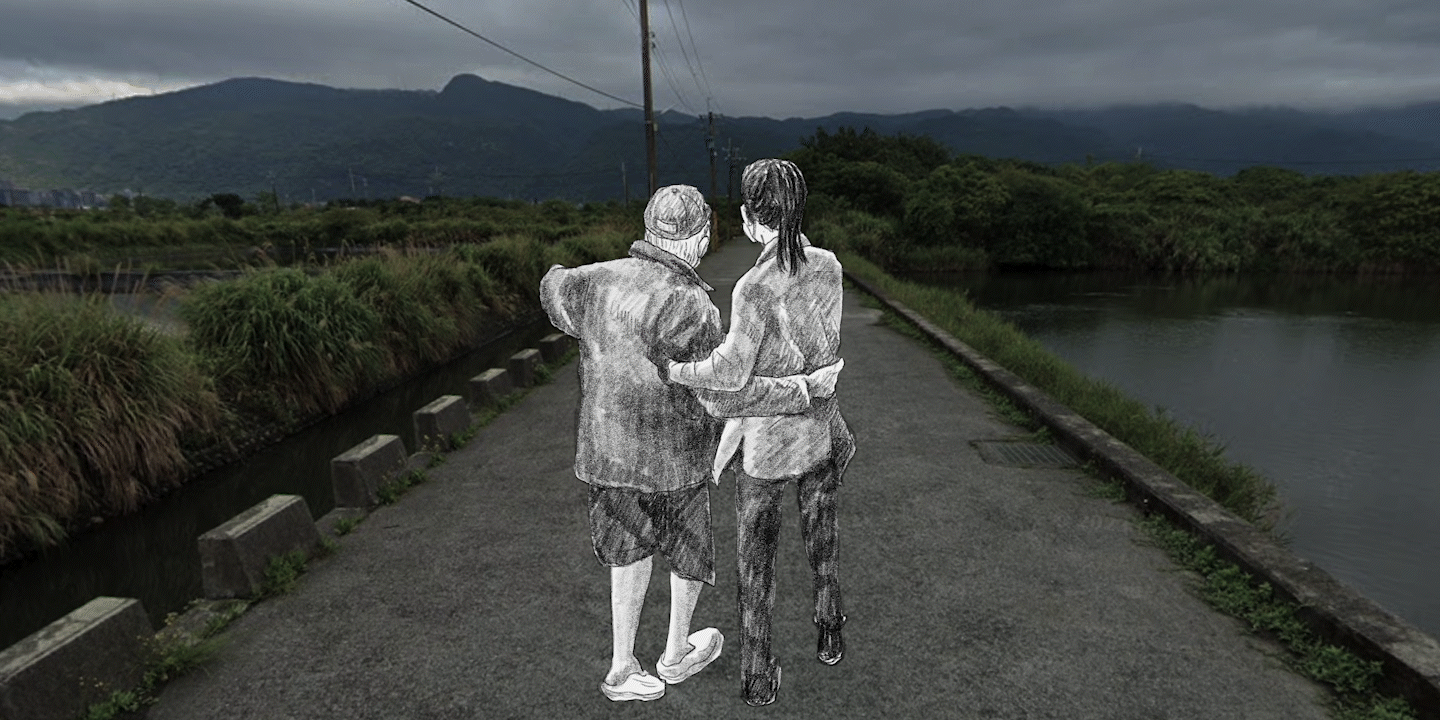一位殺人犯寫道:「經過這幾年在監獄的時間,我深感悔悟,我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原諒的罪,給被害者家屬和我的家人、社會添麻煩了,我很抱歉。」、「出監後,我將聽從家裡的安排,去親戚的餐廳努力工作;並且,希望衛生局人員陪我去看醫生,讓我服藥控制情緒;希望警察定時來家裡查訪我,讓家人和社區放心。」
看到這段話,你心裡有什麼感受?
如果你是負責假釋審查的委員,你會讓他通過假釋嗎?
這是因殺人罪入獄的小天在假釋申請書上寫的內容,監內的工作人員看到這篇說明書後,臉上揚起滿意的笑容,認為他「再犯可能性低」。
但對於小天的陳述,我卻感到非常詭異,因為他的回答非常完美,完美到好像他清楚監獄工作人員、家人,甚至整個社會對他的期待是什麼,然後配合演出。
在這些大家想聽的標準答案背後,存在許多未知:他真的對別人感到抱歉嗎?他真的想去親戚的餐廳上班嗎?如果真的通過假釋,剛離開高度戒護的監獄,他真的想要繼續受到衛生局和警局的管理嗎?
他的真實想法是什麼?
悔過書是反省後的真心話,還是作文大賽?
我想起《教出殺人犯:你以為的反省,只會讓人變得更壞》這本書。
這本書的作者岡本茂樹是日本著名的更生專家,曾在監獄擔任輔導人員、參與受刑人更生工作多年。他提到,如果有人犯下「重大犯罪」,旁人理所當然地覺得這個人要「反省」。而就我了解,無論在日本或台灣的矯正機關,輔導受刑人的方式多是要受刑人寫下文情並茂的反省作文,列舉自己做錯哪些事、有多後悔,並宣告永不再犯。
岡本茂樹認為,許多受刑人小時候遭到虐待、霸凌、疏忽、壓抑、性侵等不當對待,長大也沒被好好善待過,被撕裂的身心始終沒有結痂、被治癒。這導致他們大多無法信任身邊的人,遇到問題不知向誰求助,常常就這樣走上歹路。因此,在「悔過」之前,必須先讓長期處於壓抑狀態下的受刑人釋放情緒,看見過去的創傷。
岡本茂樹不再強制要求受刑人寫悔過書,而是以「給添我麻煩的人」為題目,請受刑人具體寫下哪些人會讓他們產生負面情緒?在和對方相處時發生了什麼事?又帶給受刑人們哪些困擾?
有一位受刑人因受黑道大哥指派殺人,而犯下殺人罪入獄;在寫以「給添我麻煩的人」為題的信時,他決定寫給死者。一開始,這封信充滿了對死者的批評和埋怨:「如果不是因為你先做出妨礙我們組織的事,我也不會殺了你」、「我因為殺了你,現在進了監獄,我一直很恨你」、「我會被逼得這麼慘,都是你害的」。沒道歉,甚至還責怪被害人,這封信讀來毫無悔意。
但在寫信過程中,岡本茂樹慢慢引導這位受刑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。原來,他小時候在學校被霸凌,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向父母求助後,卻得不到任何幫助,反被要求「自己想辦法解決」。
而在他逃家加入幫派時,裡面的大哥很照顧他,「我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溫暖。」他說。所以當大哥要他去殺人,並對他說「萬事拜託了」,他覺得自己是被大哥託付重任,自然願意執行幫派要他做的事。
經過這段對過往人生的梳理,信的最後,受刑人對被害者寫道:「雖然我寫了都是你的錯,但我知道奪走你性命的事不會消失」、「我知道說再多你也不會原諒我,真的很對不起」直到這時,他才真正發自內心表達對被害者的歉意。
看完這本書,我理解到一個人不再犯的關鍵並非寫悔過書,而是需要被理解與傾聽,感受到自己被好好對待,才能知道覺察他人生命的重量。於是,我也嘗試用這個方法,跟前面提到的受刑人小天互動。
「你為什麼做出這件事?」
我先透過數次會談,和小天建立關係,進而了解他的成長經驗、生命中經歷過哪些創傷、哪些事物帶給他壓力。
小天畢業於設計相關科系,一開始在家接案工作,但案源少、收入不足以支撐生活,於是小天的媽媽叫他去外面找工作。小天曾進入一間設計公司,但沒有同事要主動帶他熟悉工作環境,「相較同期進來公司的兩位女生,我是男生,又是一個肥宅。」他自嘲地說;小天說,碰到不會的工作時,沒人教他,後來就離職了。小天也曾去清潔公司面試過,但肥胖的身軀耐不住又熱又累的清潔工作。每份工作都做不久,在外工作頻頻碰壁的小天,決定躲回家裡。
這一躲就是好幾年。
小天每天在家看電視、吃飯、睡覺。一個正值青壯年的工作人口,卻長期失業,對於這段履歷上的空白,小天自有一套對外的說詞:我要留在家照顧中風的爸爸。然而,當我進一步細詢小天爸爸的病況,發現爸爸其實只是不方便外出,需要他人幫忙買飯、備餐而已,而且這項任務也是由媽媽來做。
看著兒子整天在家無所事事,小天的媽媽不斷催促他找工作。而小天覺得媽媽不理解他碰到的挫折,導致兩人的摩擦越來越嚴重。
原本,小天是有朋友的。他曾有一群相熟的國中同學,常常一起出去玩。但後來同學們開始吸毒,他也跟著吸,結果被警察抓到送強制勒戒。這時,媽媽出面幫他繳了罰款,並要他和壞同學斷絕往來,他在媽媽的面前,把手機裡同學們的社群帳號一一封鎖。
而小天在日常生活中的最後一個朋友,是在當兵時認識的同袍X。兩人退伍後時不時會聊天、出遊,後來X無預警斷聯,再次得到他的訊息時,是警察打來說X犯下某起案件,問小天是否知道X的行蹤。後來,小天如實跟媽媽說這通來自警察的電話內容,媽媽告訴他,就算X來找他,也不要跟X聯繫。
媽媽宛如小天人生中的守衛者,想幫兒子擋下所有會帶來「不良影響」的人;小天也聽媽媽的話,沒有再跟這些人聯繫。但他不擅社交,生活中有互動的人變少,也沒有再交到新朋友;碰到求職壓力,他不知道可以找誰聊,只能和媽媽整日在家面面相覷。隨著與媽媽的摩擦變多,溫暖的家變成壓力鍋,鍋內壓力不斷升高。
終於,他受不了了,他喘不過氣、快窒息了。但沒錢、沒辦法搬出去獨自生活,小天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入監:他想,在監內不用擔心生活費,又可以和媽媽保持距離。於是,小天拿了一把刀,捅了住家附近餐廳的店員。
後來他跟法官說之所以犯案,是因為「店員態度很差」。如果結合他過往的經歷來看,小天對店員不滿的情緒背後,藏著長期失業和外表帶來的自卑,因而認為大家都瞧不起他,以及無法應對媽媽要他找工作的要求,種種壓力積累膨發。
犯案後,小天自己走到對面的警局投案。「終於解脫了。」他說。
我問他:「是因為捅人宣洩壓力,感到解脫了嗎?」
他說,是因為終於可以從家中的壓力鍋逃出來,「我真的走投無路了。」
監所悔過書寫得好 但監所外的犯罪風險仍在
經過偵查訊問、羈押到開庭審理,小天最後被判處數年有期徒刑。小天服刑多年後,到了申請假釋的時間,然後,他就寫了這篇文章一開始提到、被監所人員認定「再犯可能性低」的假釋說明書。
但是,小天這次持刀攻擊店員並不是第一次犯案。多年前,他就曾犯下另一件重傷害案件。兩起案件背後,都存在小天依賴家庭無法獨立,以及與母親摩擦多、促使他想逃離家裡的狀況。
在小天入監期間,他與媽媽之間也持續著矛盾的親子互動。住在家裡時,小天的媽媽一方面一直催他出去工作,另一方面仍不斷提供他生活費。服刑期間,小天媽媽常常來監獄探視他,每月寄數萬元生活費給他,這讓小天在假釋審查中的家庭支持項目獲得極高的分數。小天因為有跟被害人和解,被認定為「犯後態度良好」,但這也都是小天媽媽幫他去和被害人家屬談和解、賠錢,他本人從未和被害人家屬說過話。
如果小天沒有學習如何正確因應壓力,做好情緒管理,和媽媽的互動模式也沒有改變的話,他是否仍可能再度犯案?下一次,會不會犯下更嚴重的罪行?
「沒感覺」 不代表沒問題
從犯後悔意、出監規劃、和被害人完成和解,到家庭支持等假釋評估項目,小天都獲得良好的分數,因此,他極有可能通過假釋,即將出監。
雖然一個人犯罪與否會受到很多因素影響,但我決定從自己可以協助的地方做起。面對小天的處境,我希望先協助他理解自身狀況、正視和媽媽不健康的互動關係。
我請小天寫一封給媽媽的信,並特別叮囑:「這封信裡不用和媽媽道歉或道謝,只要寫出你對媽媽真實的感受就好。」在這封信中,小天寫到之前我和他討論的出監就業規劃,提到出監後會去就業服務中心找工作;如果找不到工作,也會去職訓局上課。他信中寫下「這幾年都是我不會想,才會犯罪,我會好好努力改變」、「我不應該繼續造成你的困擾,成為家裡的累贅」等字句。
接著,我請小天寫第二封信,「假如你是媽媽,會寫什麼樣的信給自己?」。而小天寫道:「我一直催你去找工作,都是為了你好。我年紀越來越大了,沒辦法養你一輩子,希望你找一份穩定的工作、不錯的女孩,結婚生子,讓媽媽不用再為你操心。」
從這兩封信可以看得出來,小天認為媽媽的所作所為是為了孩子好,反而是他自己有問題,才會造成犯罪行為。他將媽媽對他的期待和要求內化,把許多「應該」和「不應該」捆束於身。而當我問他在寫這兩封信、或回想與媽媽互動時有哪些感受,他總是回答「還好」、「沒什麼感覺」。
接下來,我開始和小天練習怎麼辨別開心、難過、焦慮、不安等各種情緒。我們常以在監所碰到的事件為話題,開啟討論,例如我會問他「同學在舍房和你分享會客菜時,你的心情是什麼?」、「同學在工場拿你的身材開玩笑時,你的感受是什麼?」等等。希望透過這些談話,協助他掌握對情緒的感知能力。
感受自己的痛 才有機會理解他人的傷
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,我們重新談回小天和媽媽的互動。
小天說,他了解媽媽要他工作是為他好,「但當我跟媽媽說之前工作遇到的問題時,媽媽說的話讓我覺得,她不理解我遇到的困難、否定我的感覺,好像這都是因為我不夠堅強、不夠努力。」
原來,小天曾跟媽媽說過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難,例如:在設計公司上班時,遇到疑問想請教同事,對方卻總是不想理會;因為體型的關係,「你和哥哥幫我找的清潔工作、洗碗工都要久站,我沒辦法。」
小天跟媽媽說「我想工作」,也想傳達自己對工作的挫折感:我覺得很不容易。
但小天的媽媽是在1980年代辛苦打拚成功的人,她覺得這些都是藉口,給出的回應是:「我都可以做到,你為什麼做不到」、「你已經造成家裡的負擔」,繼續要他找工作。
在這次談話中,小天向我坦誠他對自己的想法:「我之前找工作失敗很多次,因為沒什麼專長學歷,長得胖又不好看,每次面試被拒絕都讓我很挫折。」小天說,「我常常想,是不是我整個人都有問題,我的存在就是個錯誤。」
聽完小天說的話,我一方面很欣慰經過這段時間的學習、引導後,他覺察及表達情緒的能力有很大的進步。但另一方面,也為他對自己的評價感到惋惜。
「媽媽覺得是為了你好,才做這些事,但她可能不知道如何用對的方式,表達對你的關愛,所以有時候會說出讓你感到受傷的話。」我對小天說,「現在,你已經學到怎麼覺察、表達自己的感受了,未來我們可以嘗試和媽媽說出你的想法,讓她知道該怎麼和你互動,讓她知道,愛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。」
「不要覺得自己的感受沒什麼大不了的,如果連你都覺得自己的情緒不重要,那誰會覺得你重要?」出監前,我認真地看著小天的眼睛說,「請記得,你是值得被愛的。」
我們容易把所有罪犯貼上窮凶惡極、不知悔改的壞蛋標籤,把他劃定為本質上的邪惡,加以高聲撻伐、猛力砸石,這樣就毋須耗費心力尋求問題與解方。但他們也有可能是從未被好好對待,而不知如何善待他人的人。如果沒給過他任何協助,沒和他一起努力嘗試,怎麼知道他有沒有悔改之心、有沒有教化可能?
在海裡載浮載沉許久的人,或許在等待你手中的救生繩:當你擲出繩索,他將緊抓住彼端,奮力爬上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