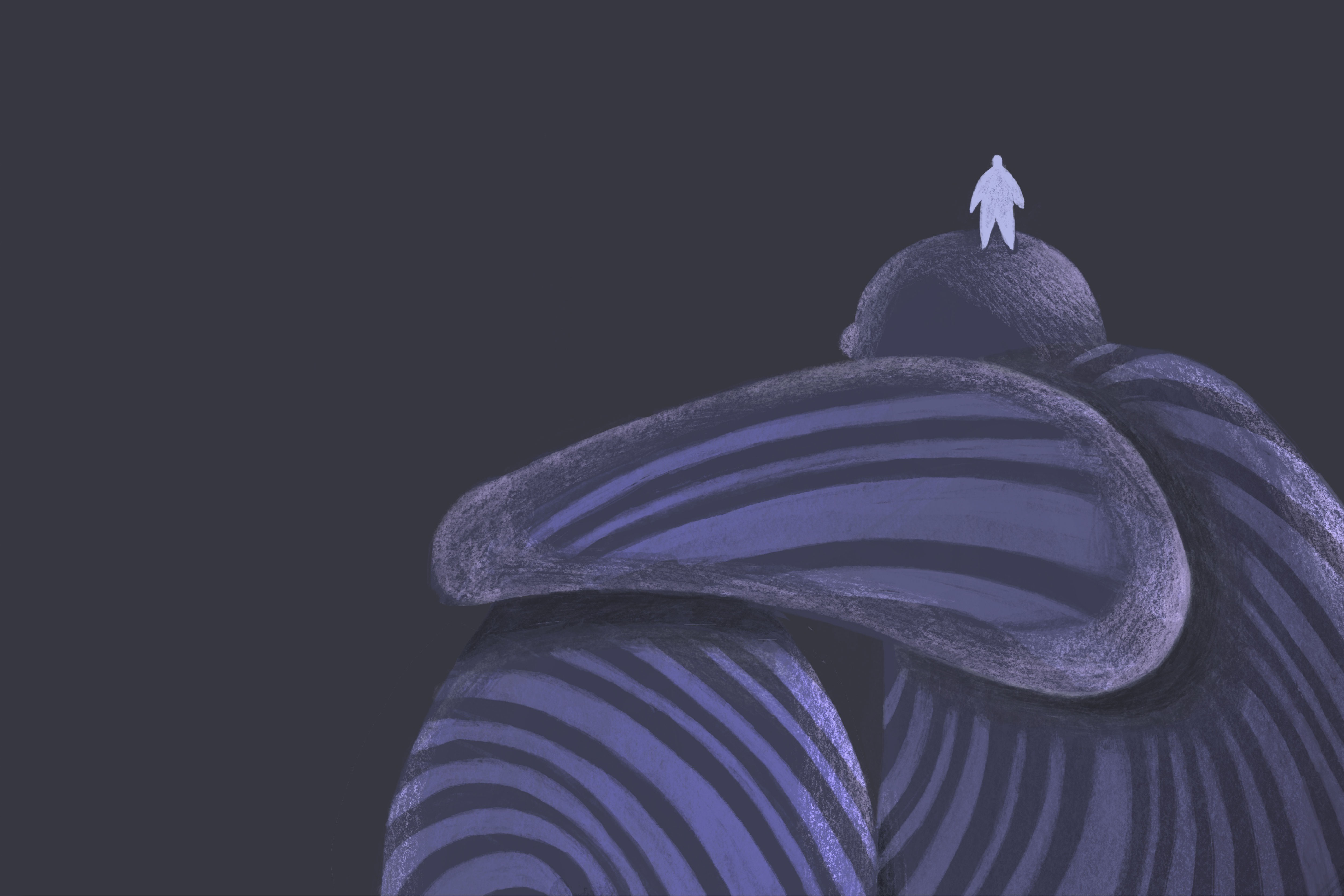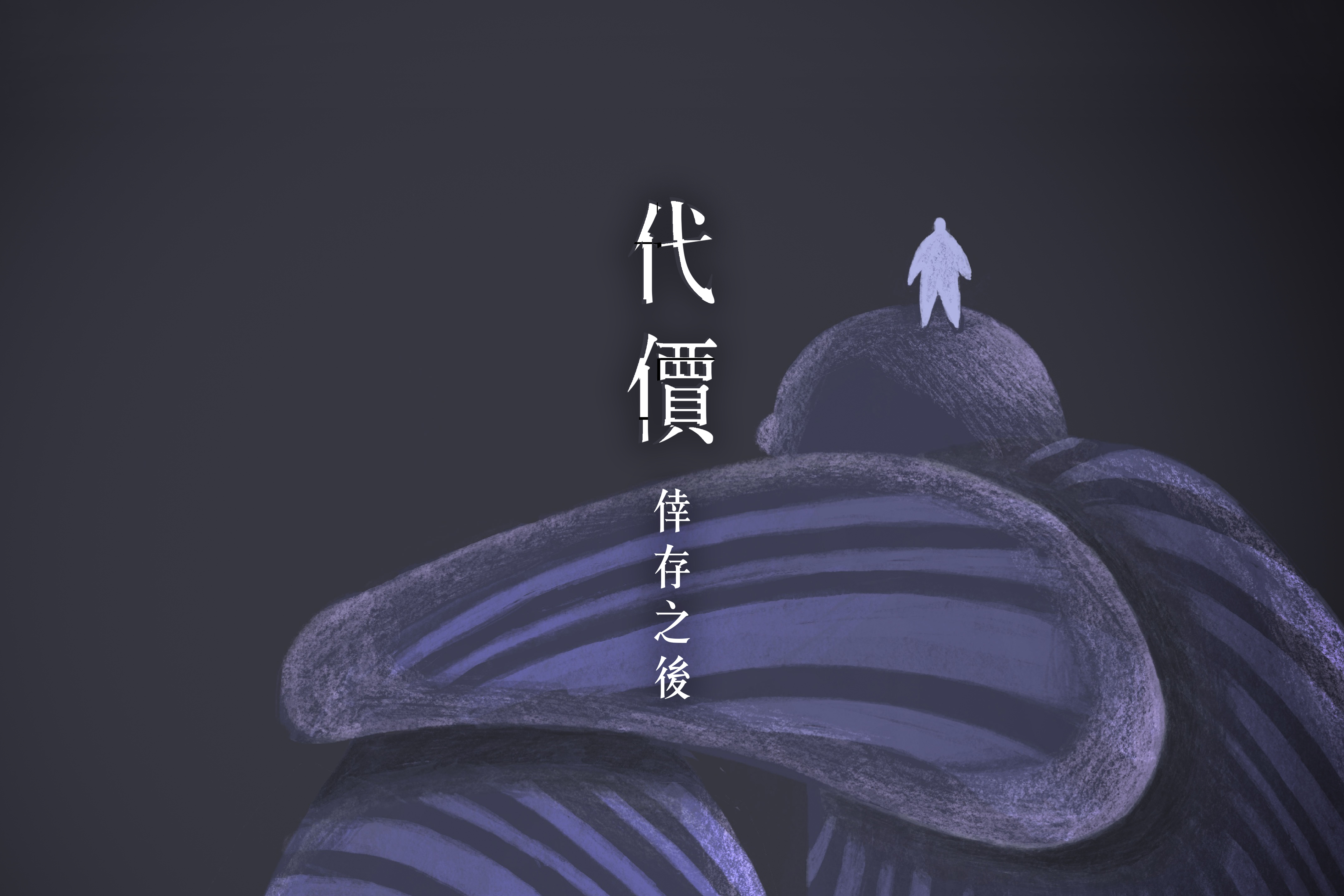本文涉及談論性暴力議題,恐造成閱讀者替代性創傷,未成年者不宜閱覽,成年者請斟酌自身狀況評估是否繼續閱覽。
教官趕到後,帶我到學區的派出所報案。「我們等下去前面的派出所喔。」「等下員警會載你去醫院。」我任由教官帶我去警局備案、員警帶我去醫院驗傷。過程中沒有人問我要不要報警,沒有人告訴我之後會發生什麼事。
在我開口、向學長說出我的遭遇之後,這一切就自動地發生了。這些都不在我理解與預期之內。是法律、體制自動向我走來;這過程是如此粗糙,讓我疼痛不已。
醫院驗傷:彷彿被外星生物強姦
在醫院急診室,護理師帶我到診間。坐下後,她先要我填寫個人資料,接著詢問我各式各樣的問題:什麼時候發生的?對方有戴套嗎?來之前有沒有洗澡?有沒有抵抗,像是用指甲抓對方之類的?
我說,前一天對方有逼我用嘴巴,再前一天他有進來。我沒有抓對方,我沒有抵抗。我心想,好像應該要抵抗的,護理師好像期待我要抵抗。
印象中,護理師要我把長褲、內褲脫下。「內褲也要!」她特別強調。接著要我坐到一張血色的皮椅上。「唰──」一聲,粉色的布簾拉上,只剩下我自己。我把衣服褪下,用指尖把內褲拎到旁邊的籃子,把長褲疊好,壓在內褲上。
我坐在皮椅的前側邊邊,雙腳併攏在一起。
護理師進來後,指示我把雙腳放在椅子兩側扶手處的小架子上。我遲疑了好幾秒,擔心兩腳各放一邊,不就等於被大家看光光?
那是我第一次做婦科檢查,身體有點不自在。
「再坐上去一點!雙腳再開!再開!對。」護理師連聲催促。我的大腿內側似乎快抽筋了。護理師開始擺弄燈光,所有的光源都集中在我的陰道,我感覺自己的陰道在那一刻被用放大鏡檢視。
後來護理師把一爿粉紅色的小簾子,立在我的肚子上,我不再看見自己下半身的裸露,也看不見男醫師的表情。老實說,我鬆了一口氣。
可是下一秒,一個冰涼的東西進到我的陰道,並逐漸撐大。男醫生要我「放鬆」,但這實在很難──有一個金屬質感的東西在我的陰道裡,把陰道撐大,有棉花棒還是什麼的在陰道壁上刮弄。我感覺自己好像在被外星生物強姦。
內診結束後,我獲准穿上褲子。護理師再度問我,是否還有其他對方碰觸過的地方。我想了想,我跟護理師說,他還有親我胸部。我撩起衣服,小小的棉花棒繞著我的乳頭轉了兩三圈。驗傷結束後,護理師似乎說了性病檢查的通知事項。我無法認真聽,陰道跟胸部冰冷的感覺還殘留在我的感官和腦袋裡。
依照現行規定,若是在七天內遭受性侵害,警方會要求倖存者到醫院驗傷,檢測是否懷孕、染上性病,更重要的是,留存證據。舉凡陰道冠(俗稱處女膜)有無撕裂傷、陰道是否驗出被告體液,都要仰賴第一時間到醫院驗傷採檢留下的證據。
由於檢驗需要進行陰道內診,如果倖存者沒有心理準備或內診經驗、醫護也沒有適當的說明各個步驟及必要性,內診採檢過程會極為難堪與難受,非常容易就聯想到性侵害經驗,並感受到類似的傷害感受。
聽到我驗傷的遭遇,一位在南部醫院服務的資深醫務社工G表示,在平日上班時間沒有醫務社工陪同就做性侵驗傷,肯定不符合規定。「我一定會把驗傷的器材擺出來,一個一個解說,尤其是內診的鴨嘴。因為這個過程是很傷害的,即使我生過小孩,我都覺得那個很難堪。」社工G認為,在採檢的過程因為涉及身體的碰觸,更需要有細緻的解說,才能確保倖存者身心都已有準備。
此外,醫療人員的態度也至關重要,勵馨台北分所社工B說,自己曾碰過服務個案去急診室驗傷時,急診室護理師大聲地說:「你就是那個性侵害個案吼,你去那邊坐。」當場讓服務個案被門診區的所有人盯著看。社工B強調,這不是只單一個案,還有其他倖存者也碰到類似的經驗。
在驗傷時應該需要隱私、隔離的操作,讓倖存者清楚知道不會有其他人會聽到檢查時的對話、猜到發生了什麼事。這需要醫護人員理解倖存者的創傷,知道倖存者在這時更需要隱私的「創傷知情」素養。
警局筆錄:反覆被質疑有沒有說謊
從醫院回來後,我被帶回派出所做筆錄,在員警平時辦公的桌子旁,是一個開放空間,旁邊的人都可能聽得見。筆錄開始後,警察對我發出一連串的問句:
發生在什麼時候?凌晨?凌晨幾點?對方是誰?是這個人嗎?他對你做了什麼?你有反抗或掙扎嗎?你們是什麼關係?有情感關係嗎?你為什麼跟他們同住?黑社會背景?他有說是什麼會或什麼幫嗎?你說一周幾次?
員警問,我就答。我盡我最大的努力,讓自己表現的冷靜又正常。當時的我以為,要讓自己看起來有條理又堅強,才能營造我是個「配合的當事人」。
可是當筆錄結束後,陪我到警局的媽媽把我拉到一旁:「剛剛筆錄時,你為什麼笑得那麼開心?」我說,因為覺得這一切都要結束了,所以很開心。可是媽媽說,我的笑可能被誤會,「剛剛警察就有在講,怎麼來報案,還笑得這麼開心」。
我不知道,連笑都是一種罪。
根據警署規定,每個警政單位都要有性侵害專責人員,且每年必須有6小時的教育研習。但6小時的研習究竟足不足夠?一位在台北婦幼隊的員警表示,婦幼隊每天都接觸性侵害的案子,所得知識已經超過這6小時。但她也認為,對於某些單位來說,一年可能只有個位數的案件,甚至數年才需要做一次性侵害筆錄,對於訊問、筆錄注意事項,不如專責人員熟悉,就需要透過研習再複習,因此專業度相比於婦幼隊,確實有所落差。
由於分局、派出所不只受理性暴力案件,就相當仰賴各個承辦員警對於性暴力案件的敏感度,如果有幸遇到有「創傷知情」、同理創傷反應的承辦員警,真的是種福氣,能降低許多不必要的二度傷害、社會審查與自我責備。
舉例來說,勵馨台北分所一位社工B就轉述,七、八年前陪一位未滿16歲的小男生去分局做筆錄,員警不斷確認他是否犯罪,他明明已經說了事實;那位警察還說:「我現在把錄音關掉了。你老實跟我說,你到底有沒有做?」
勵馨台北分所的社工B也轉述其他兒少倖存者筆錄時的負面經驗,負責員警問倖存者:「你要告的是性侵害,這個罪很重喔,你確定事情是這樣?」孩子告訴社工B,明明他已經說了實話,還要一再反覆確認,甚至質疑是不是說謊,內心很受傷。
走上法律途徑,做筆錄是必要的, 台北婦幼隊一名女性員警解釋,「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」這些問題上法庭也會再問一次;她們也會盡量站在被害人的立場,對這些問句加以解釋,像是:「我想知道為什麼你沒有馬上說出來呢?考量是什麼?」
然而,對於倖存者來說,做筆錄的過程要反覆回想受暴經歷,過程中的保護與尊重,往往會因為人力、空間、專業、行政流程等造成二度傷害。
在最理想的「減述」制度下,倖存者只需進行一次筆錄,不必反覆重述痛苦記憶,但現實並非如此。
每次重述受暴經歷都是一種傷害
在完成第一次筆錄的兩個月後,我又去了分局補做第二次筆錄。那名員警重新問了事件細節,還說因為我提供的電話錄音,他聽不懂,要我自己打逐字稿。即便我一聽到那個男人的聲音就想吐,我還是撐著,把那些逐字稿打完。
其實,目前的法律規定有「減述」規定,在未成年、心智障礙者或或特定情況下,可以減少被害人要重複陳述筆錄的次數。減述的特色在於,在報案一開始即讓檢察官指揮,包含筆錄問什麼、該朝向哪個方向蒐證,都會讓檢察官決定。由於檢察官已經知悉案件,便毋需在警察局、地檢署一再重述筆錄內容。
不過,台中家防中心的社工E說,法令要求「減述」的保護意義,在現實的偵查中仍然無法落實。採訪中,許多社工都提到,「幾乎不可能只做一次」,不論是被告有了新證詞需要核對,還是第一次筆錄沒有詢問到的細節要再補齊......,各式各樣的理由都可以要求倖存者再次陳述,再次召喚不願再想起的回憶。
要避免被害人重複陳述所帶來的二次創傷,並兼顧司法偵查的查證要求,實屬兩難。
新北家防社工D認為,即使進入「減述」程序,仍可能相隔兩、三個月後再開偵查庭,問題可能和警察筆錄的問題相當接近,「要倖存者再說一次細節,最後往往變成一種『測驗』──為什麼倖存者在警局說這樣,在地檢署又說得不一樣。」
地檢署:「當可輕易呼救......」,不起訴
隔幾個月之後,檢察官叫我到地檢署開偵查庭。我們在一個有L型沙發跟茶几的房間「聊天」,檢察官叫我放輕鬆,照實回答就好。
然後,又是一連串的問題:你們第一次的時候,你反抗了嗎?你可以抓他、踹他下體、跳下車,為什麼你沒有? 你說對方以一星期2到3次的頻率對你施暴,你能證明嗎?
檢察官還不忘提醒我:「對方有請律師,要小心講話,要小心被告。」
我聽到我說:「有一次合意,其他都不合意。」我好像看到檢察官嘴角的笑意。
不久後,偵查結果出來了:不起訴。
果不其然,不起訴書上寫著,嫌疑人聲稱我們是交往關係,我是因為無法平衡自己被當成小三才會報警,而且他的女朋友從頭到尾都知情。相比之下,我的證詞薄弱太多。
我能理解因為沒有足夠證據,所以無法起訴。但我憤怒的是,檢察官陳述的這些理由,潛藏一種暗示──「當我受傷,我會逃跑,沒有逃跑就是沒有受傷。」
這些理由,我不服氣。
早在民國88年,刑法第221條修正時,就將性犯罪的「致使不能抗拒」更改為「違反其意願」,但這樣的觀念卻仍潛藏在各式各樣不起訴書或判決書中。所以必須證明傷痕,要有傷痕才能證明「不能抗拒」。但「違反意願」又該如何證明?
根據統計資料,約有一半的妨害性自主案件會被檢察官以證據不足而決定不起訴,一旦起訴,被判刑的機率就有七成。性侵害作為一種「密室犯罪」,在證據稀缺的情況下,不是無罪,就是3至10年的有期徒刑。倖存者的證詞勢必被用放大鏡檢視,在法庭上也勢必會被攻擊。
勵馨高雄的社工F也說,她有位個案到男性友人家吃飯後,先被男性友人毛手毛腳,後來遭到性侵。「檢察官就問倖存者:『當對方開始對你毛手毛腳,你有機會離開,為什麼你當時沒有求助?』那位倖存者對這句話相當在意,一直詢問我,她是不是解釋得不好?」
除了要面對外界對「不求助」的質疑,倖存者的證詞也常會受法官及檢察官的臆測。
紀姓家事律師就說,曾遇過有當事人因為把性侵過程描述得相當清楚,結果法官或檢察官認為描述過於特定、清楚,因而質疑當事人蓄意說謊,事先都編好了,才會這麼清楚。另一種情況則是當事人被性侵時意識不清,在第一時間陳述時記憶很片段,後來又想起更多的細節,卻被質疑是加油添醋。
記得清楚、記不清楚,都不可以。
勵馨台北的社工B表示,一旦到了法庭上,人證跟物證都會被「去脈絡化」地檢視,會把口述的記憶當作是一個物證,反覆檢驗跟考驗這個「物證」的質地。「那對於我們的個案真的是很痛苦,因為他就已經不想回想了,可是還是要被逼迫要講得很細。」
律師黃致豪也說,當性侵受害者被加害者當作一個施暴物件的時候,是一種物化,「當人進入了司法程序,那是另外一種物化。」如果又遇到很糟糕、沒有性別意識的警察、檢察官、法官,整個司法程序就成了體制化的傷害。
倖存者:只是想求助,一定要被通報嗎?
根據現行的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規定,當醫院、學校、村里長、警察、社工等單位得知有疑似性侵害的案件時,必須在24小時內立即通報主管機關。
因此只要倖存者對外求助,無論個案的意願如何,都需要被向上通報,如果有明確的人事時地物,多數情況都會被送交給警方,進入司法程序,而性侵害案件又屬於「非告訴乃論」,因此進入司法程序後,無論倖存者願不願給外人知道這件事,都得配合做筆錄、驗傷、出庭,由不得倖存者說「不」。
不過,許多社工也提到,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規範通報義務,但沒有罰則,所以仍然存在可以不通報的模糊地帶。但對於未成年的性侵害案件,若未通報則會違反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》遭受處罰。
的確,採訪中的每個社工都會提到,確實會遇到有些被害人只是想對外求助,停止被侵害就好,他們不想進入司法制度中,只想早點結束身心折磨。
現行制度下,倖存者一旦對外求助,學校、社工、警察等單位都有通報義務,自動進入司法程序。倖存者的消極應對措略,包括可能是不到警局應訊、做筆錄,警察會在兩次傳喚不到後,移交給地檢署。檢察官可能因為案情不明確,就此簽結。但究竟「案情是否明確」,取決於檢察官,當事人無法置喙。
在收到檢察官的不起訴書後,我有七天的時間可以決定要不要申請「再議」,我決定,到此為止。
不申請再議的理由很複雜。包括我缺乏證據能證明他對我的操控,也難以面對司法體制對我的反覆檢視。這些都讓我在絕望與希望間擺盪,我已不想再困在不堪回首的噩夢裡,不知何時才能醒來。
我想,就這樣吧。當初告訴學長的時候,我也只是想離開受人控制的生活;走上司法調查與訴訟,並非我的選擇。
停下吧。我不用繼續承擔更多司法拷問,也可以如願回歸本來的生活。停下吧。
然而,焦慮、害怕並沒有消失。往後長達七年的時間,每當我看到與「那個男人」體型相似的男子,我總會不自覺地心悸,旁人問我為何突然臉色慘白,我無法回答。創傷復原之路,如許漫長。
【代價:倖存之後】系列報導
本專題報導為 願景工程 – 2022 獎助採訪伴飛計畫 獎助作品——
願景工程於2022年舉辦「獎助採訪伴飛計畫」,提供每件作品獎助金,協助想要寫出好報導的人,完成報導任務。歷經超過半年的打磨,完成作品陸續和讀者見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