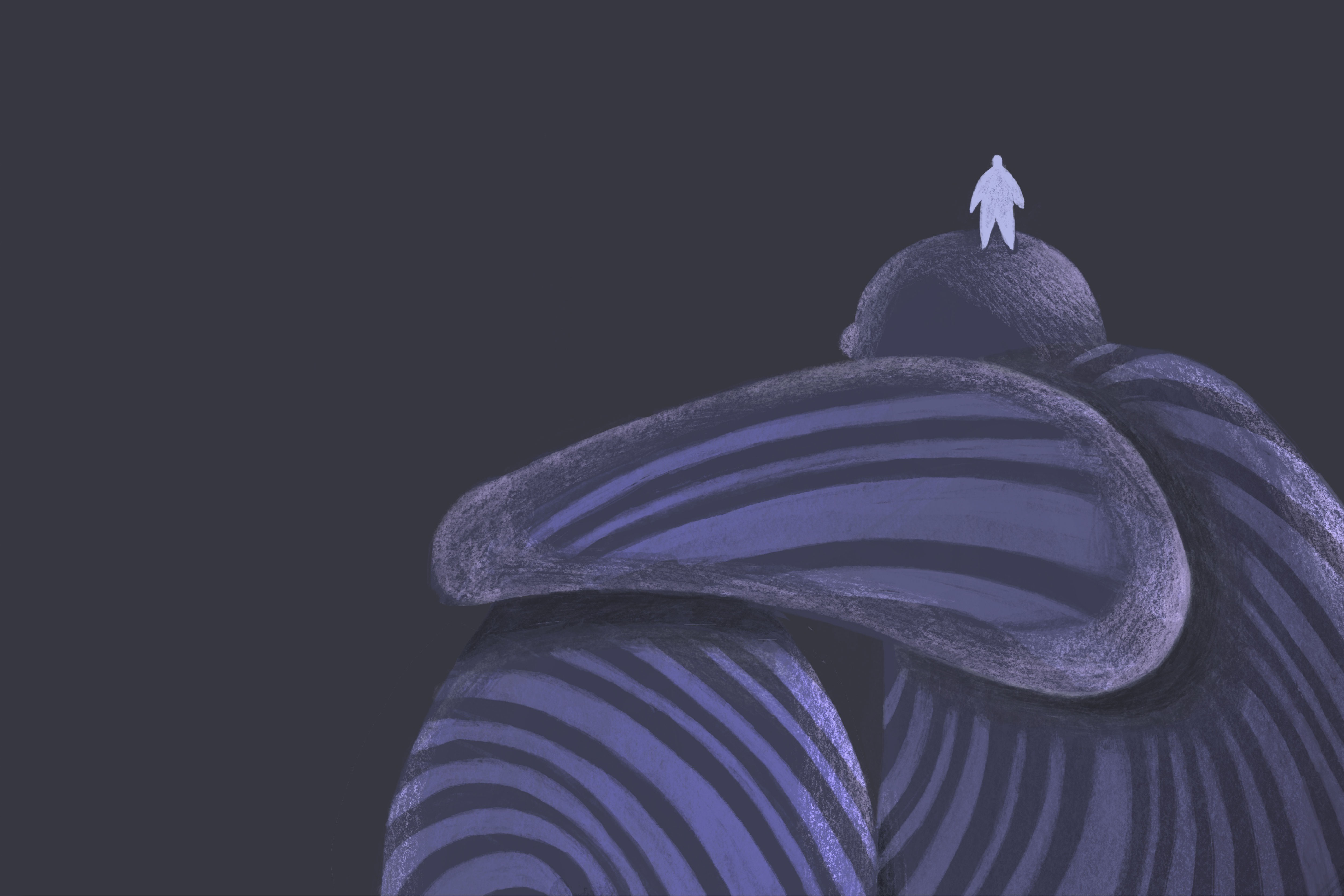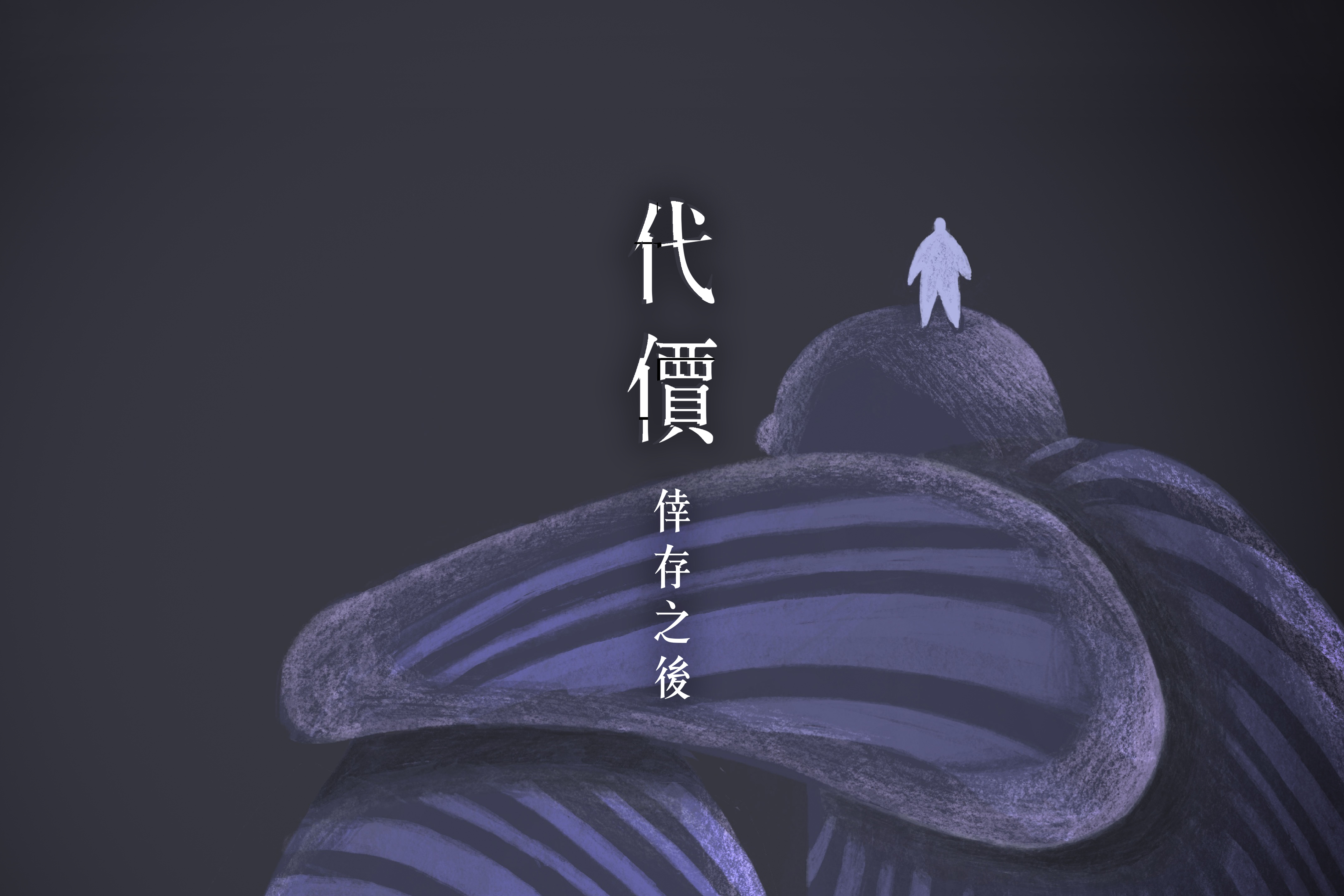本文涉及談論性暴力議題,恐造成閱讀者替代性創傷,未成年者不宜閱覽,成年者請斟酌自身狀況評估是否繼續閱覽。
我原本以為報警之後,自己就能脫離那場惡夢,回歸正常的生活。然而,焦慮、害怕並沒有消失,往後長達七年的時間,每當我看到與「那個男人」體型相似的男子,我總會極度焦慮、在路上看到與他的車子類似的汽車,我都會低頭加速遠離。種種的「創傷後症候群(PTSD)」症狀一再地襲擊我,直到八年後我才漸漸走上復原的道路。
心理諮商:她也不知道怎麼幫我
在報案的兩三天後,學校幫我安排了一位諮商中心的心理師。一周一次,我會到諮商中心,在大概兩坪的會談室裡,和心理師聊上50分鐘。在十幾次的會談中,我只記得那位心理師很常反問我:「為什麼?」
舉例來說,有一次會談,我談到自己「底線很低」,只要狀況不危及生命,我就能夠忍受,不過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心理師就回應:「對啊,為什麼呢?」那天我們的討論就到那為止。
每次在諮商中心會談結束,我總需要花上一個星期的時間,消化我在會談室接收到的疑問:「為什麼呢?」原來諮商是這樣的嗎?充滿反覆詰問與千百個為什麼。
報案後半年,我從諮商的過程逃走了。我跟心理師說,可能要轉學。她便俐落地結掉我的案子。
社工:一通電話就結束的協助
回想起來,在報案幾天後,社會局的社工也有打電話給我,她說,因為接到通報,所以打來關心我。她問我:「你需要什麼協助嗎?」我說:「應該沒有吧。」她確認學校已安排心理師給我後,我們便結束了對話,再也沒有連絡過。
後來我才知道,那句「應該沒有」,讓我錯失與社工討論案情、個人諮商、律師補助、庭前準備的機會;我也錯失在法律上完整表達自己看法的機會。
事實上,社工能做的事情很多:可以陪倖存者驗傷、做筆錄,協助通報家防中心、評估安置需求;若有需要法律、心理諮商的協助,社工也能連結相關資源,幫助倖存者向政府或其他合作機構申請補助。
這些是社工能做的事。但當時的我完全不知道。我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,因為我連自己可以得到什麼都不知道。
不知道如何向外界求助,是我的錯嗎?
「資訊」經常是倖存者最缺乏的東西。無論成年與否,很多倖存者可能都和我一樣,對於性侵害的法律規範和權利救濟一無所知。
律師黃致豪曾經說過:「99%的被害人在接觸到公權力的時候,沒有辦法有資訊知情權。」如果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,哪些是法律上的義務與權利,倖存者才能在衡量之下有所選擇。有所選擇,才能認知到自己有力量,而這正是復原的關鍵。
新北家防性侵組社工K就認為,當倖存者進到通報系統,接收服務時,不僅僅是被動接收,而是能「選擇是否接受、接受哪些服務」,才能拿回自己的主控權。
不過,K也說,以目前每位社工的工作量,社工很難主動去瞭解每位個案所需要的協助;特別是沒有表達求助意願的成年個案,案子通常很快就結掉了。
根據衛福部規定,一位保護性社工每月的合理工作量約為25案。但我訪問的家防中心中,有些縣市的社工服務案件高達40至60案,幾乎是合理負荷量的兩倍以上。
每個月有40案會是怎麼樣的狀況?以每個月工作22天計算,每個倖存者所能分到的時間約是半天。若是40案中有新開案,需要訪視、陪同偵訊、陪驗傷等需要更長的工作時間,那麼其他個案能分配到的時間就會變少了。
身上揹著逾45件個案的台中家防社工E說,一天工作就是八小時,還經常加班、睡眠都不夠了;但案件一直進來,「要訪視、要調查、要提供服務、又要資源連結。」能夠留給自己的時間非常少。社工既是奔走各地、訪視個案的體力活,更是承接創傷與難題的情緒勞動,需要時間修復自我。但有時,這是奢求。
對社工來說,除了提供對人的服務,純粹文書工作的「登打報告」是沉重的負擔。政府如火如荼推動「社會安全網」的建置,衛福部要求社工每訪視一次個案就要打一次報告,本意是希望帶給個案有品質的服務,但龐大的文書工作量卻也幾乎壓垮個案量爆多的社工。
桃園家防中心社工督導J表示,登打報告是社工很大的壓力來源,因為「太花時間了」。勵馨高雄一位社工F說,「有時候社工花在電腦前面的時間,可能會比訪視個案的時間多。」
忙碌的社工無暇接住每個受傷的人
如果成年倖存者並不想求助,不同縣市不同社工有不同做法。桃園家防中心社工J說,提供倖存者該有的求助資源後,「讓他知道他可以再回來找我,不會因為結案損害他的權益。」
另一位新北家防中心的社工D則表示,若是個案沒有明顯的求助意願,或是個案狀況相對比較穩定,就會很快地走到結案。
採訪過程中,許多社工都提到「社會安全網」的諸多要求,使服務倖存者的過程更加困難。衛福部訂定的服務量、開案量、通報量等績效指標,未必能反映個案的真實需求。
當社工與績效數字、時間賽跑時,倖存者可能就成為被迫配合的工具。
或許正是因為社工的人力不足,我才會遇到一個很忙、一聽到我說「應該沒有」,就此結束協助的社工。當初如果他能告訴我,我依法能有什麼權益,或許我就能少掉許多折磨。
長達七年的自責與自我厭惡
在報案以後,我過了好長一段意識渾沌的日子:每天都以為自己會死,走路時希望被車撞飛;瞥到與痛苦記憶的相似之處,腦袋就開始自動重播,一遍一遍問著自己:如果當初我做了、或不曾做什麼,一切會不會不一樣?
我始終害怕異樣的眼光,卻渴望溫暖的擁抱;我總是很快地進入曖昧或交往關係,卻無法打從心底信任別人。在性暴力事件發生後的五年中,我交往過八個伴侶,最長一年,最短一個月,都是我提分手。
我難以愛人,當對方說愛我、喜歡我,我會聽而不聞。認為那只是他們不夠瞭解我。一旦他們知道真實的我,就不會再喜歡我。儘管在交往前,我都會吐露自己的受暴經驗,但我從沒真正相信過他們溫暖的反應。我無法打從心底信任別人,無論是點頭之交、家人、朋友、還是情人。
在往後的性經驗中,我的身體總是被迫想起那段揮之不去的受暴經歷。我以為自己可以透過其他經驗去覆蓋過往之惡,我曾沉迷於性快感,卻愈來愈憎恨自己的身體。
我討厭自己一撫弄就潮濕,也討厭自己喜歡被綑綁的性癖。我討厭自己嗜痛的體質,也討厭自己喜歡強勢的性愛風格。我討厭自己喜歡性愛。一旦將這些快感與曾經的強暴經驗連結,我就會不自覺噁心想吐。
我怎麼可以喜歡上,近似於強暴的性愛?每次高潮彷彿都在告訴我:我活該。
我花了四年的時間近乎狂熱的懲罰自己,幾乎滿檔的打工,讓疲累把自己壓垮;獨自一人騎上六、七小時的車,追尋孤獨的平靜。我從未覺得自己真的好起來過,似乎一直停留在18歲,永遠沒有長大。
事發九年之後,我才終於理解,原來我在強暴中受過一次傷,在向外求助的過程中再受一次傷,這些傷痕深刻影響著我與世界的互動。不是只有我,許多遭遇過性侵害的倖存者,往後的情感、性關係,總存在著難以跨越的牆。
勵馨高雄的社工F告訴我,性侵害的倖存者所受到的傷害,不只是性暴力本身的傷害,更多是情感關係上的傷害;當倖存者帶著困惑成長,人生後來的朋友關係、人際關係、親密關係,也都會跟著受傷。
期盼我的故事能幫到更多性暴力的倖存者
從18歲到現在十年了,經過了這麼多年的自我責怪與自我憎恨後,我才終於能夠理解,自己所遭遇的是所謂的親密關係性暴力,類似家內的性侵關係。
他對我實施的是典型的性誘騙,先是逐步讓我喜歡上他,用漸進的肢體動作讓我產生「他是不是喜歡我?」的幻覺,性侵我後,再利用我對他女友的愧疚感,讓我不敢聲張,讓我陷入自責、「不知道自己在幹嘛」的狀態。
諮商心理師跟我說,「他在找一個獵物,而你天時地利人和成為了那個獵物。在那個局裡面,你只是一個小朋友,怎麼可能知道自己在這個局裡面?今天成人都不一定知道自己在這個局裡面。」
心理師說,從她多年在性侵害領域服務的經驗,漸漸認知到「倖存者需要認知到過去的傷害,不是來自於自己犯錯,而這往往具有重大的意義。」
新北家防中心社工D也說,所謂復原,就是可以接受過去的自己,開始有一點點能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僅此而已。
曾任婦幼組主任檢察官的楊碧瑛曾處理多起家內性侵案。她說,有些加害者是阿公、爸爸或哥哥上,受害者當時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那是性侵害、那是犯罪,直到有一天長大了,某個契機,才會理解到:啊,原來那是什麼。
她說,當事人常因為時間久遠、而失去證據,或是記憶模糊,導致最終司法的審判不如預期;也有可能檢察官跟法官都相信他的說詞,但是在法律上就沒辦法判加害者有罪。
訴說性侵事件,不是要聽別人指點我:「如果當初如何如何,就不會發生這些事情了。」我花了許多的年歲,才終於弄清:是他的意圖、他的行為、他對我的控制與傷害,才是問題的根源──錯的是他、而不是我。
也唯有我願意放過我自己,才能真正地走上復原的道路。
復原之路,如此漫長。當我在25歲那年終於可以向周遭的親朋好友、向大眾說出經歷,才發現我一點也不特殊——受到性暴力的人何其多!我是比較幸運、已經脫離危險處境的那個。
2022年,我在網路創立了「暖暖Sunshine」平台,期望有一個性侵害倖存者的匿名社群,可以不帶批判、譴責地交流,討論自己在求助時遇到的困難,討論司法系統的流程或經驗,討論關係中「合意」與「不合意」的錯綜複雜。
發生性暴力後,世界彷彿沒有光明。平台之所以叫做「暖暖Sunshine」,是希望在黑暗的日子裡,也有一束微小的陽光;即便受過傷,倖存者也有力量,能夠自助、互助,也能閃閃發光。
【代價:倖存之後】系列報導
本專題報導為 願景工程 – 2022 獎助採訪伴飛計畫 獎助作品——
願景工程於2022年舉辦「獎助採訪伴飛計畫」,提供每件作品獎助金,協助想要寫出好報導的人,完成報導任務。歷經超過半年的打磨,完成作品陸續和讀者見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