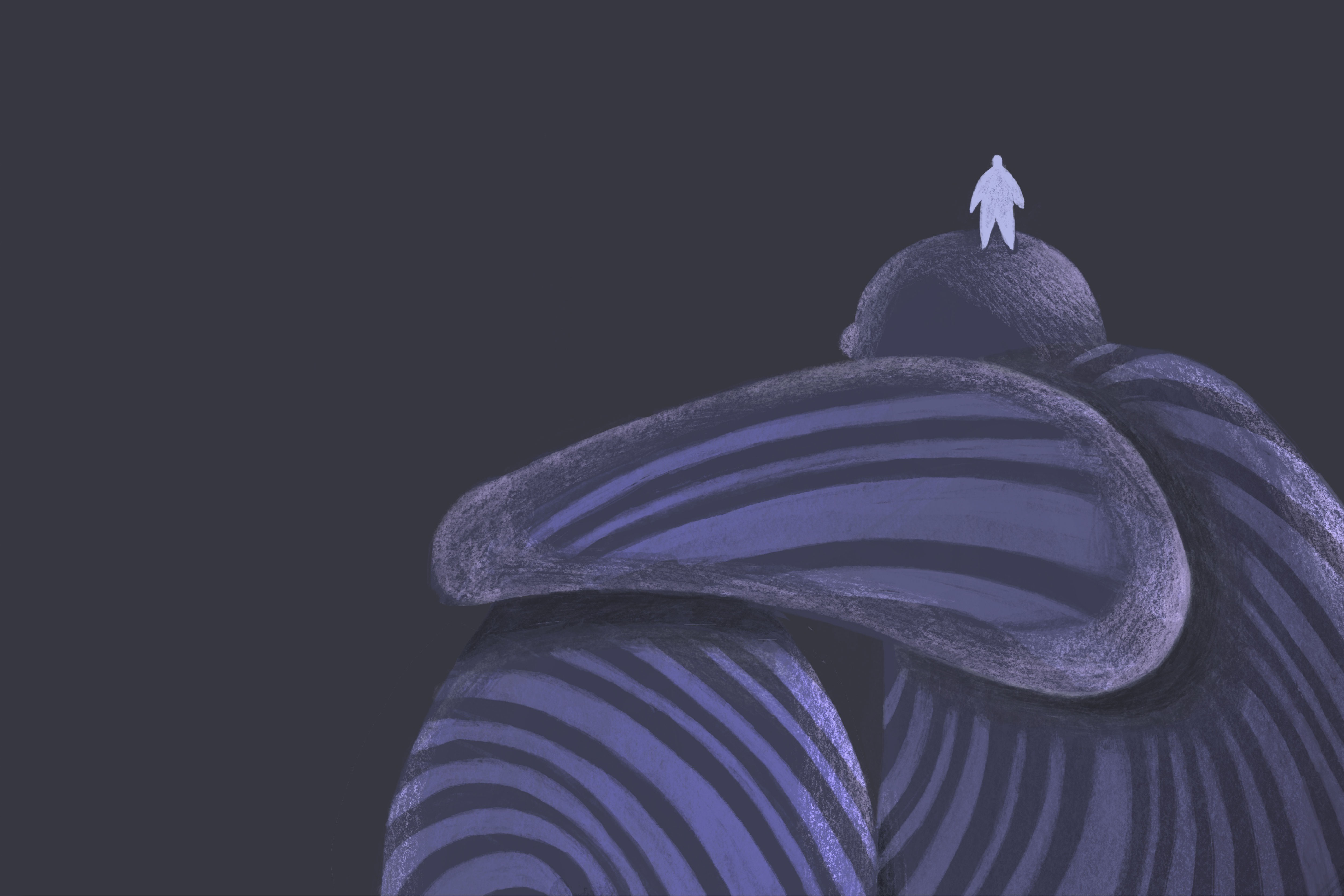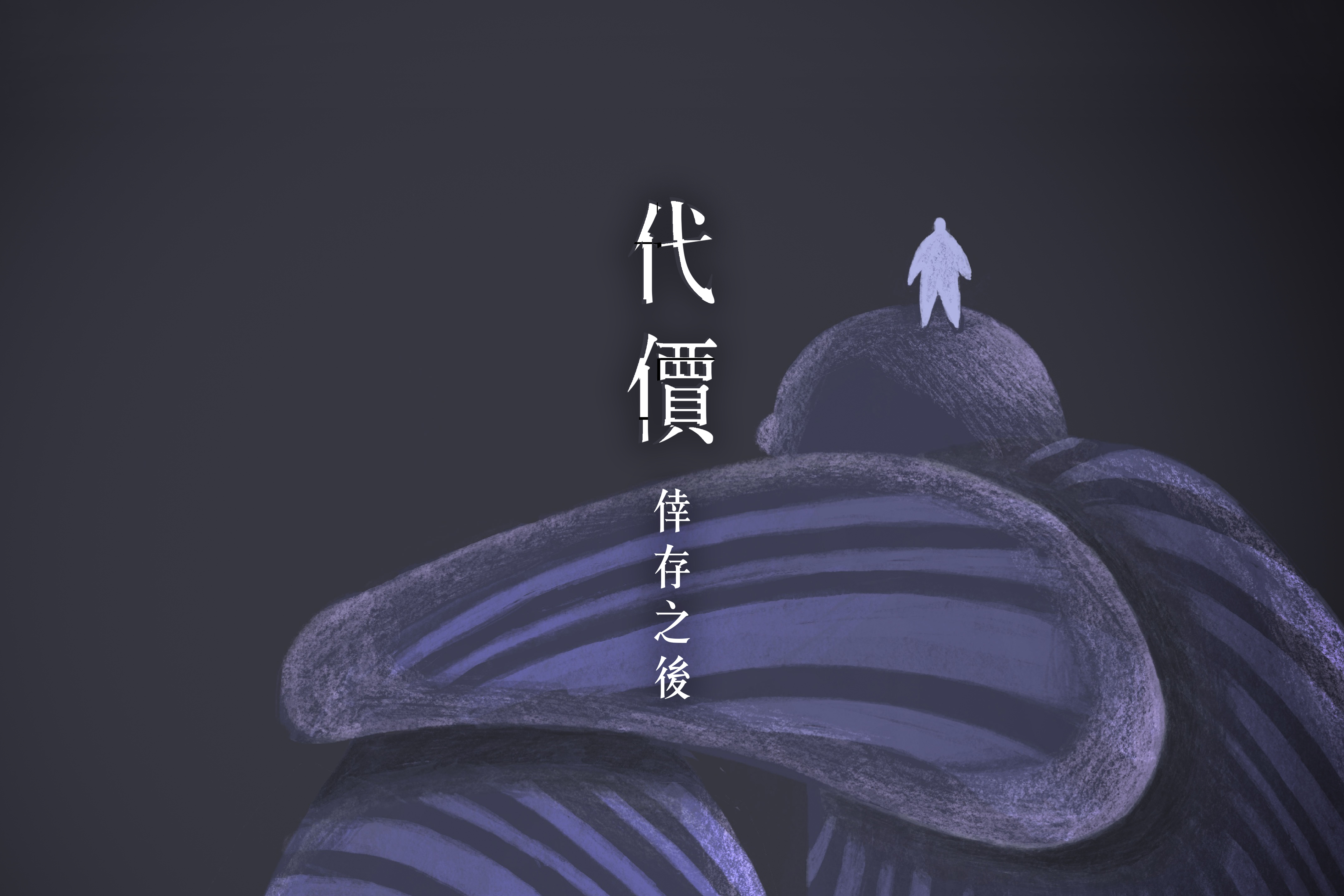警告:本文涉及描繪性侵過程,恐造成閱讀者替代性創傷,未成年者不宜閱覽,成年者請斟酌自身狀況評估是否繼續閱覽。
在外公住的那棟房子裡,外公會把阿狼帶到儲藏室、房間、廚房──無論是哪裡,總之是當下沒有其他大人在的地方──開始摸阿狼的胸部及下體。接著脫掉褲子,將生殖器放到阿狼的身體裡面。
外公從不避諱在小孩面前展示性行為,阿狼遭受侵犯時,有時表弟表妹會旁觀。阿狼也不是第一個受害的孩子,同輩表兄弟姊妹跟阿狼提過,外公對他們做過一樣的事情,甚至阿狼媽媽小時候也曾被侵犯。
阿狼今年已經23歲,想起當年發生的一切,他說當時覺得外公的行為很奇怪:「我一直不知道他為什麼要『尿』在我的身體裡。」但外公要阿狼不要跟其他人說,他覺得要尊重長輩,沒有多言。
直到小學五年級,阿狼在課堂上學到「性侵害」的概念,才驚覺:「這件事情好像發生在我身上耶!」等到外公又想拉他走的時候,他拒絕了。外公沒有再強迫他。
外公的行為停止了,阿狼也沒跟其他大人提起這件事。但國一某天,阿狼在科任課上因為身體不舒服趴在桌上休息。科任老師發現後,找阿狼過去聊聊,結果他不經意間向老師透露,外公之前會對他做一些「感覺不是很好」的事情。
這件事,就此不再是秘密。
通報那天,世界天翻地覆
阿狼回憶,當時科任老師一聽完,就說他要先跟班導師講,後來又換班導師找自己了解詳細狀況。導師聽完後,跟阿狼說法律規定要通報,不然老師會有連帶責任。「他就去通報了。」阿狼說。
根據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規定,對於疑似遭受性侵害、性騷擾的學生,老師需要進行「校安通報」與「法定通報」。前者是向教育部的「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」通報;後者則是透過衛福部系統,讓所在縣市的「家庭暨性侵害防治中心」得知並介入。
這個秘密從阿狼五歲開始,已經跟著他八年。老師猝不及防的通報,讓阿狼的生活迎來天翻地覆的改變,他不得不面對所有人的目光,24小時內,媽媽、老師、主任、警察都知道「阿狼疑似被外公性侵」。
做筆錄時,阿狼一度覺得好混亂。檢察官仰賴阿狼提供證詞,阿狼卻早已將這些回憶摒除在腦海之外。因為長年遭受性侵,阿狼早早就發展出自己的防禦機制──解離。當他的身體感受到外界的危險,就把自己的感覺收回來。當阿狼被問到事件發生後的感受,他通常會說「忘記了」或「我沒有感覺」。
然而,做筆錄當下,所有問題都要求阿狼必須記得所有細節。「其實我也不知道頻率跟次數到底多少,我真的是記不清楚啦……他們(指檢警)一直很想知道持續多久、細節之類的,我就講不出來。我(當時)只是一個國中生,要我去描述這麼多東西,太難了。」阿狼回憶。
早知道就不要講了
做完筆錄後,阿狼從此再也沒有踏進外公家。如果通報當下,阿狼還住在外公家,他有可能要面臨「安置」的命運,離開熟悉的居所,到陌生的「安全」的地方,遠離加害者。
當事件爆發,孩子可能會因為外在的劇烈變動和情緒壓力,懊悔地跟社工說:「早知道我就不要講了。」因為一講,自己的世界就變了。
在教育現場服務超過20年的學校社工師A提到,當家內倖存者說出自己被性侵的事實,可能會受到家庭內部的壓力,要求「體諒」。例如加害人下跪、哭求原諒,或是其他家人勸說「誰沒有做錯事呢?」、「他喝醉了」等話語。企圖用孝道、情感的羈絆,否定倖存者最一開始的求助。
阿狼和母親也碰到來自其他家人的壓力。雖然性侵案件屬於非告訴乃論,但是阿狼的舅舅曾來勸說不要提告,覺得這是家醜,走訴訟讓更多人知道很難聽。其他親戚也認為阿狼媽媽不孝,竟然告自己的父親。
但是,即使娘家人反對,阿狼的媽媽堅決要提告。阿狼媽媽說,自己不惜任何代價,也要將傷害女兒的人送入牢獄。更讓她難以忍受的是,自己的父親當年也性侵了她,她忍了下來,以為長大、以為離家,這一切就「正常」了。但是父親竟然也沒放過孫女。
「我已經受害了,結果我女兒沒有保護好,也讓他受害。所以我覺得這次一定要把他保護好,不能再讓他受傷害。」她堅定地說。
有了媽媽的支持,阿狼覺得自己獲得一股力量。但是,其他可能也曾被外公性侵、或目睹過性侵過程的孩子,不願出庭當證人。阿狼說,自己曾偷偷聽到其他親戚說:「不會啦,我女兒沒有那麼笨(才不會也受害)!」阿狼只覺得荒謬。
法庭的二度傷害
即便阿狼有了母親的支持,他有勇氣走入司法程序;但是在訴訟過程中,他要面對讓倖存者與嫌疑人共處一室以詰問的「交互詰問庭」。
在這個刑庭中,法官將聆聽倖存者與嫌疑人被律師、檢察官訊問的證詞,以此形成心證,決定審判結果。
在交互詰問庭中,對造律師問阿狼:「小女生的陰道這麼小,怎麼可能容納成年人的陽具?」法官制止了這段問話,否則,當時國一的阿狼就要回答這個問題。
在阿狼的情況中,法官制止律師的詰問自有法律依據: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第25條規定,如果被告或被告的辯護人在審判時,對被害人做出性別歧視的陳述或舉動,法院應該立刻制止。
那天,雖然朋友的律師提出異議,但法官認為與案件相關,允許被告律師繼續提問。朋友抓住我的手,微微顫抖,還吞了身心科醫師開給的緊急備用藥,以舒緩焦慮。
在法庭上,倖存者經常被質疑的問題還包括:證詞前後不一致、為什麼沒反抗、為什麼事後舉止如常等等。新北家防中心的社工D說,自己會安慰倖存者說,檢察官必須再確認一些細節。但她覺得,這些詰問與其說是再確認,更像是一種「測驗」。
曾擔任加害人辯護律師,也曾任倖存者告訴代理人的律師黃致豪認為,司法講求證據。但在性暴力案件中,「既然證據這麼難以取得、這麼難以保存、這麼少有證人存在,這條道路注定是非常痛苦的。」他說。
隔離訊問流於表面
根據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第23條規定,性侵害案件訴訟期間,可以採取聲音、影像傳送等隔離措施,將被害人與被告隔離訊問。避免倖存者在審判期間,還要跟嫌疑人打照面。
阿狼雖然不用在法庭上見到加害人,但在進出法庭時,他和媽媽仍會低下頭、遮掩面容。阿狼媽媽說,這是因為怕在法庭外撞見身為加害人的父親,而且不只是女兒怕,「連我都會害怕見到他。」她說。
原來,時間及刻意遺忘,並不能讓曾發生的傷害,消失不見。
但就算安排了隔離訊問,實務上也不見得都能做到。新北家防中心性侵組社工D說,她曾遇過檢察官把嫌疑人排在倖存者之後訊問;倖存者結束訊問後,一打開門,就會毫無心理準備地撞見加害嫌疑人。
還有一些法院因為設備老舊,雖然設置了隔離訊問室,仍無法讓倖存者待在裡頭放心訴說。勵馨台北分所社工B說,有些法院的訊問室僅有一道單面鏡(單向透視玻璃)隔離,雖然嫌疑人不會看到倖存者,但倖存者可以清楚看到隔壁的嫌疑人,引發倖存者的恐懼、焦慮。
我什麼時候會好?
阿狼的案件最終判刑確定,阿公被判刑八年六個月。從這個角度來說,這場官司的確制止往後可能的犯行:讓加害人進入監獄,不再侵犯家族的其他人。但法院認定僅發生過一次強制性交,其他都視為「沒有足夠證據可以證明」,這點讓阿狼耿耿於懷,也覺得很受傷。
司法調查結束後,阿狼還是噩夢不斷。他自殘、拔頭髮以對抗紊亂的內心,也開始遊走於各大醫院的身心科;甚至因為自傷、嘗試自殺,數次入住急性精神病房。
阿狼媽媽總是親自陪他到醫院拿藥。自性暴力通報至今,已經過了十幾年。這段期間,阿狼媽媽試過一小時四千元的身心科特別門診,只為了讓女兒跟醫生多聊一點。
並不是每個親人都能理解阿狼的身心狀況。阿狼的爸爸就難以理解:阿狼跟阿狼媽媽都曾被同一人性侵,為什麼阿狼媽媽好像活得好好的,阿狼反應就這麼大,還會得憂鬱症?
勵馨執行長王玥好指出,創傷反應因人而異,「有什麼樣的反應都很正常」,不能要求倖存者有一種良好的「標準反應」。
阿狼換過四個以上的諮商心理師。諮商時,阿狼會像答錄機一樣,不帶任何感情地重述自己遭性侵的遭遇。阿狼發現,有些諮商心理師不太敢碰觸和性侵有關的話題,偶爾提一下這件事,卻又沒有要更深入處理的意思,這讓阿狼對諮商並不那麼信任,國中之後,就不再諮商了。
曾任勵馨中部蒲公英中心的諮商師May認為,諮商師要與倖存者建立信任關係並不容易,但信任是開展晤談的重要基石。她也曾無意間迴避倖存者話題,即便她當時已經進入蒲公英中心工作,但在真實的諮商中,真要碰觸沉重的傷痛,即使有多年專業知識打底,她當下還是會不知如何啟齒,懷疑自己該何時、如何碰觸傷口。
過去的陰影揮之不去,阿狼的身心壓力慢慢累積,在大四那年爆炸。
大四某天起床後,阿狼突然感到渾身無力,他硬是花了最後的力氣,離開大學所在的城市,搭了三個多小時的火車回家。回家後,「就變得很像廢物喔!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。」阿狼回憶。當時阿狼狀況低落到吃飯需要別人餵,洗澡也需要別人代勞。
後來在媽媽支持下,阿狼重啟每月一次的心理諮商,光是由學校回到台北諮商,交通來回就要三小時。阿狼媽媽會全程陪同。
這次的諮商經驗,不再只帶來挫敗的感受。阿狼以前陷入解離狀況時,會把自己的感受切分開來,避免受到傷害。這種「失去感覺」的狀況持續多年。但諮商後,「(感覺)才有比較回來一點點。」阿狼說。
不過,這有好有壞。阿狼覺得「感覺回來」的優點是比較能感受到別人的關心,但當情緒海嘯襲來時,又會很痛苦,「有時會覺得自己很髒,或自己好像不值得被愛」。
勵馨高雄蒲公英中心的心理師芸兒(化名)形容倖存者的解離狀態,宛如「活在一個透明的玻璃罩裡面」,雖然可以看到外頭,但與外界總是隔絕;等到玻璃罩被拿起,裡面的倖存者才能重新跟世界連結。
「當玻璃罩被拿起,會感到痛苦和害怕是很正常的;過往倖存者待在玻璃罩裡,雖然和外界隔絕,但也會獲得一種安全感。」芸兒說,揭開罩子之後,接下來,就是一條新路,要讓倖存者和身邊的支持系統一起攜手走下去,重新建構和世界連結的方式。幸運的話,新的人生,也就如此展開了。
【代價:倖存之後】系列報導
本專題報導為 願景工程 – 2022 獎助採訪伴飛計畫 獎助作品——
願景工程於2022年舉辦「獎助採訪伴飛計畫」,提供每件作品獎助金,協助想要寫出好報導的人,完成報導任務。歷經超過半年的打磨,完成作品陸續和讀者見面。